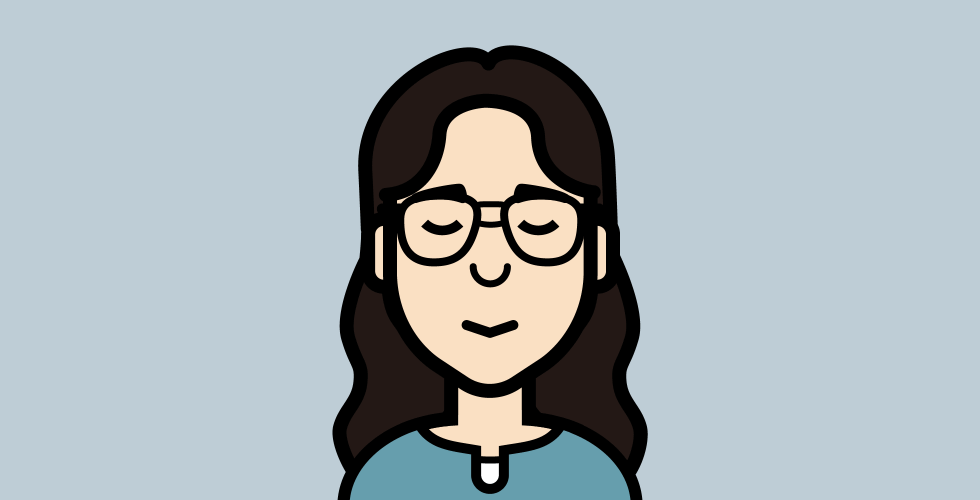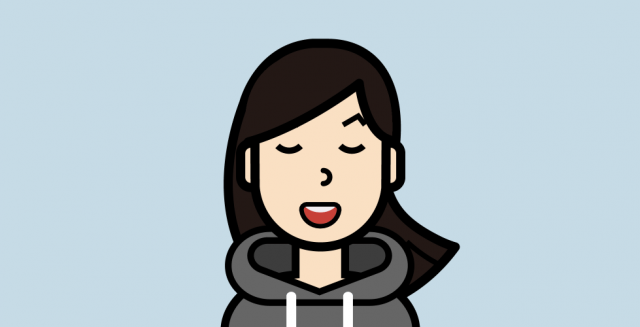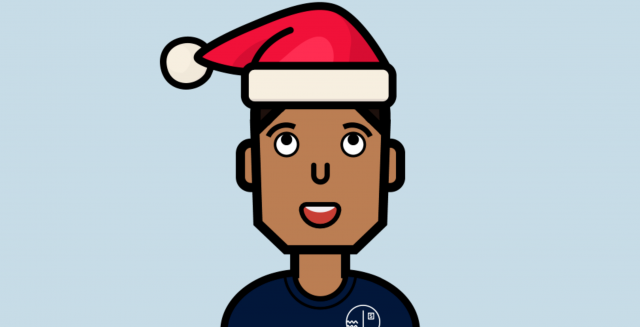JoMarcH-L
献给 anna。
“So, if you are hopeless romantic like me, I think we could be good friends.”
后来我想,”hopeless romantic” 是一切的契机。那是一个很小的网站。我写去了
一个将 hopeless romantic 作为个人最鲜明的色彩的女孩,现在住在爱尔兰,
德国女孩,离故乡足够远,与我爱慕的孤独足够近。
信寄到的时候是早上 5 点,我在 8 点寄去了回信。天如混浊的大海,
我感觉那可能是我写过最长的一封信了,就像回应一封遥远的情书。
和 mette 的一拍即合是当下时代最好的概括。热烈而带着冲动,
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。然后交换了照片。照片中的她抱着吉他,脸上
一封信只写给一个人看。反复推敲的每一句话一旦寄出无法再修改,
后来啊,后来。我们去了邮局。我贴上千里江山图的邮票,把厚厚一
我无数次告诉她别再熬夜了。因为全世界最令人憎恶的时差把我的早
我可以安心地把我想到的一切告诉她。我觉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。我
交流美与关于美的一切早不再需要做任何修饰。它们都浮夸。
一个故事就说出来了,一幅画就说出来了,一场脑海里的舞就说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