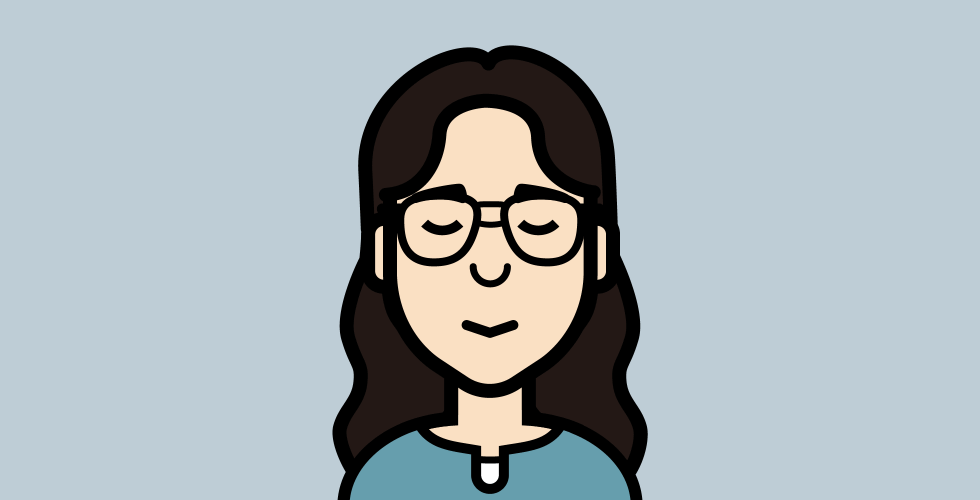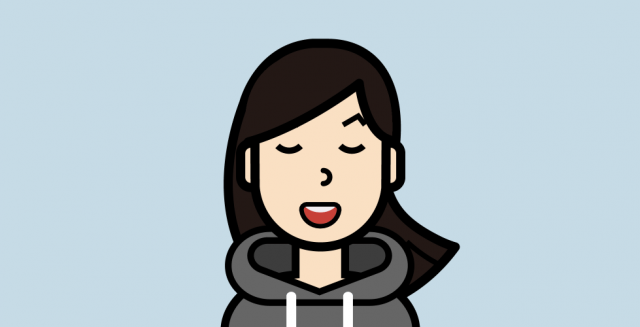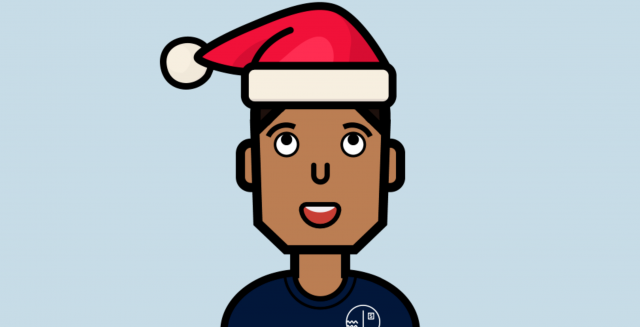原文以簡體中文撰寫,由OpenAI翻譯。
獻給 Anna。
「所以,如果你像我一樣是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,我想我們可以成為好朋友。」
後來我想,「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」是一切的契機。那是一個很小的網站。我寫了第一封信,通過那個網站從中國寄到愛爾蘭,花了整整 25 小時,等待回信的那幾天似乎從未如此漫長。我也說不清為什麼這個詞讓我輾轉反側,但幸運的是,她最終寄來了回信。
一個將「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」作為個人最鮮明色彩的女孩,現在住在愛爾蘭,正處於少女最美麗的年紀。她說她出生在柏林,是愛爾蘭的交換生。她的信很長。她談到她摯愛的芭蕾舞、鋼琴、她熱愛的文學和美術。在愛爾蘭,天際燃燒的雲彩,那種從字裡行間流露出的美麗與自由。Jane Austin 的小說,Kate Winslet 和 Saoirse Ronan 的文藝電影。她談到那些我身邊再沒有人喜愛的情節,那些我們心中熟知的台詞,以及靜默話語中的浪漫哀愁。她談到那些美麗的事物,就像她的信一樣,像湖水般安寧澄澈,讓人願意登上一艘小舟,與柔和的浪花共舞,卻又不願漂向盡頭。
德國女孩,離家鄉足夠遠,與我所愛的孤獨足夠近。
「記住,我會一直在這裡陪著你,你永遠不會孤單。」
信寄到時是早上五點,我在八點寄出了回信。天色如混濁的大海,月光照在樹梢上。
我覺得那可能是我寫過最長的一封信,就像在回應一封遙遠的情書。我們是那些抽象的、孤獨的、消逝的、美麗的共通愛人。信讓人感到安心,並心甘情願地敞開心扉,坦誠一切。
與 Mette 的一拍即合是對當下時代最好的概括。熱烈而衝動,簡潔果斷,不加修飾,我們在簡短的訊息中認出相似的靈魂片段,心甘情願地相信和愛。與 Anna 的一切屬於木心的詩句中。日色變得緩慢,車馬郵件都慢。我凌晨,她黃昏,往返一封信要三四天。像湖裡的小船一樣緩慢而不定,但我們都懂了。無法去說哪個更美好、更純粹、更惹人愛。哪個更好,哪個較差。詩越遠越美麗,信是,人也是。
我們交換了聯絡方式,然後交換了照片。照片裡的她抱著吉他,臉上有美麗的雀斑。紅髮綠眼,像凱爾特的精靈。芭蕾賦予她修長的身姿,衣著樸素但美麗,她的笑容融進了愛爾蘭的黃昏。地平線在她身後無限延伸,遠山和火燒雲氤氳不散。
一封信只寫給一個人。反復斟酌的每一句話,一旦寄出就無法再修改。我花了無數日夜去揣摩她該如何展開這封遠信,她會如何想,她會抱著什麼心情給我一個遙遠的回覆。仿佛只要向西望去,就能看見大陸盡頭窄窄的海峽,藍綠色的波浪洗盡一路塵埃。
後來啊,後來。我們去了郵局。我貼上《千里江山圖》的郵票,把厚厚的信封塞進郵筒。作為無神論者,我荒謬地祈求上帝讓它平安送達那位女孩的手中。我送她的畫中的女孩擁有和她一樣的深綠色眼睛,懷裡抱著一束桔梗花。我在信中塞滿了我能想到的一切,裝著我的城市的照片,我的明信片,我珍愛的郵票。這種不安與欣喜似乎不再屬於這個時代,但它屬於我們。她也送了畫給我。她畫了一對女孩,大約十五六歲,一個黑髮黑眼,一個紅髮綠眼,對畫外的人燦爛地微笑。
我無數次告訴她別再熬夜了,因為全世界最可憎的時差,讓我的清晨成了她的深夜。
我可以安心地將我想到的一切告訴她。我認為什麼是好,什麼是壞。我們心甘情願地向彼此坦露一些話語,一些思考,以及關於藝術的種種。我從來不用擔心她會誤解我在賣弄,也不用猜測她會在暗地裡如何評價我。我也不需要揣測哪些是客套,哪些是奉承。我們坦露一切,如白潔的信紙。在信紙中,我們無拘無束地浪漫與愛。
對美與關於美的一切的表達不再需要任何修飾。它們都浮誇。
一個故事已訴說,一幅畫已訴說,一場腦海裡的舞已訴說。甚至守著聽筒裡的靜默,無人言語,萬物空寂。我們等待彼此說完。